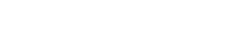徐祖耀,浙江宁波人,生于1921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材料科学家。1942年毕业于国立云南大学矿冶系,留校任助教一年;1943—1948年任国民政府兵工署材料试验处技术员、助理研究员;1949—1953年任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副教授;1953—1961年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热处理系副教授;1961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首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教授。1983—1999年任《马氏体相变》国际顾问委员、《金相学报》(后改为《国际材料表征学报》)顾问编委,1997—2003年任《日本钢铁学会会刊(国际版)》顾问编委。潜心于材料科学研究与教学近70个春秋,成果迭出,著作等身,在相变研究及材料热力学上尤见特长。率先在我国开展纳米材料相变的研究,是我国研究开发形状记忆材料(Ni-Ti基,Ni-Al基,铜基,Fe-Mn-Si基合金及ZrO2基陶瓷)的先驱者,也是材料热力学研究和教材建设的倡导人和执行者。近年来,致力于超高强度钢的设计和研发,提出淬火-分配-回火(Q-P-T)热处理新方法,颇具成效。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何梁何利奖。出版著作10部,其中《金属学原理》培育了建国后第一代材料工作者;《马氏体相变与马氏体》、《材料热力学》、《材料科学导论》和《相变原理》等著作培养了我国几代材料科学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祖耀是材料科学界的一棵常青树。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率先研究材料相变(主要为马氏体相变和贝氏体相变)、材料热力学,研发形状记忆材料,致力于超高强度钢的设计和研究,成果迭出;他积极投身材料学科教育改革和教材编写,著作等身,桃李芬芳。这位学界泰斗从求学起就立志科教兴国强国,他淡泊名利,唯用勤勉和专注献身科学,彰显耀人光泽。
“冶金强国”梦
徐祖耀先生的心中一直深藏着“冶金强国”梦。从“实业救国”到“科教强国”,至今虽已耄耋之年,他依然孜孜以求。
徐祖耀出生于宁波的一个中等经济家庭,徐家祖上曾显耀一时。据传,宁波徐氏家族从山东迁来,辈分为“文武传芳承祖德”。徐祖耀的尊叔祖传隆公在清末任正一品江南提督,被敕封为“建威将军”,传隆公晚年便居住于他修筑的“将军第”中。徐祖耀的三个叔祖均无后嗣,二叔成为大房继子,而父亲从小将徐祖耀作为二叔的继子,因此徐祖耀自小就成为了昔日提督军门的长房长孙,按清规可世袭二品官员。不过,徐祖耀的父亲一向自立门户,虽例行对长辈尽孝道,但坚持自食其力,在担任一家公司高级职员的同时,自修中医,经常为人免费施医,道德操守令人称道。这为年少的徐祖耀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徐祖耀曾说,父亲虽然很少“言传教导”他,但身教使他从小便牢固树立起了自食其力、正直处世、恪尽职守、待人忠厚等人生信条。
身处乱世中,徐祖耀从小便目睹了旧中国民穷国弱、忍辱受屈、战火肆虐、民不聊生的惨痛情状。在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使命感的驱动下,他和其他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结伴同行,贴标语、搞宣传,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唤醒大众投身抗日救国的大潮。当时,中国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冶金强国梦”就在徐祖耀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他也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祖国的兴衰连在一起。
1932年夏,徐祖耀小学毕业,考入当时声誉最好的私立效实中学,在“行忠信,行笃敬”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这为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日寇在华夏大地作威作福,高中毕业的徐祖耀受老师鼓励,决心奔赴西南内陆昆明上大学。虽然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医生,借以治病救人,而他却在“冶金强国梦”的驱使下报考了国立云南大学矿冶系。“当时人们认为重工业乃是发展百业之基”,徐祖耀回忆当初为何选择艰苦的矿冶专业时说:“我选择的矿冶业正是当时最‘重’的工业。”
踏入大学校门的徐祖耀开始勤奋学习,大学一年级成绩居全班第一,荣获“龙云奖学金”。大学四年,校园因躲避日寇轰炸几度迁徙。徐祖耀和同学们常年身处荒郊僻壤,环境艰苦,时常青衫一袭。做实验、上课堂,连正月初一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校园中的学习热情十分浓厚,当时云大矿冶系由中华基金会(美国资助)协办先进设备,大师也云集校园。据徐祖耀回忆,1938-1943年期间系里任教的教师中,有五人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孟宪民、冯景兰、许杰、袁见齐和郭令智)。在云集的大师中,有两位教师对他人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一位是系主任石充老师。他被称作当时中国仅有的一个半选矿专家中的一位,剩下的半位恰是他的助手。学校为他来校执教所进口的选矿仪器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主要设备之一。石充老师在实验室大显身手,使学生看得出神。徐祖耀的毕业论文就是将当地的贫铜矿经浮油选矿为可供冶炼的富矿,这些初步成果使他立志献身科学研究、振兴中华。第二位是蒋导江老师。当年蒋导江老师教授冶金课程和金相学课程,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每科考试只有三题,但都要求深刻的思索和总结,一般学生到考试后再加琢磨才能回答完全。当年徐祖耀对于金相学课程兴趣浓厚,倍花力气,自信能取得好成绩。但是蒋导江老师最后只给了78分,尽管这已是班上的最好成绩了。这个78分让徐祖耀印象深刻,也成了他后来不断进取的动力源泉。每当想到那个78分,徐祖耀就充满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
徐祖耀于1942年夏毕业。他所在班中有两名学生后来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另一位为殷之文)。徐祖耀留校任金相学及分析化学助教一年。回想起在云南学习的五年时间,虽然时时身处险境,但救国救民的愿望刻刻铭心。谈起他做毕业论文之事,徐祖耀总是激动不已:“中国人不笨,中国人勤劳,为什么会比别人差呢?”“中国人应该超过他们,中国人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甘心呀!”徐祖耀坚信这点。当他的毕业设计题目“浮油选矿试验”取得显著效果时,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科学救国的力量和造福国家的欣喜。
1943年秋,徐祖耀进入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兵工署材料试验处冶金组。当时,试验处处长为周志宏,冶金组主任为丘玉池(1945年后魏寿昆任主任)。在这里,徐祖耀先完成周志宏处长直接下达的一项测试任务:以物理方法(比重)代替化学分析测定硅铁中的硅(Si)含量。之后他又被奉派到28厂(合金钢厂,周志宏兼任厂长),历时半年解决了高速钢锻造开裂问题。这项成果于1944年正式投产,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钢材封锁,为抗战出了份力。
此后,徐祖耀先后于唐山交通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从事冶金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实践着自己“冶金强国”的人生信条。
甘当“教书匠”
徐祖耀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教书育人:“当教师离不开学习,教学相长,教书育人,也培养自己。”在90周岁生日庆典上,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56届学生谢锡善到场祝贺,并为徐先生送上一张珍贵的班级合影。已经年逾古稀的弟子谢锡善深情地说:“先生的学生中,至少有两人已经成为院士,分别是周邦新和柯伟。”此外还有唐山交通大学1952年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世昌和葛昌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54年毕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国良,上海交通大学1963年毕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连城。
1949年,徐祖耀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开始了“教书匠”的生涯。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立,徐祖耀于1953年调入该院执教。由于肩负着钢铁强国的历史使命,钢院的学风非常严谨,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徐祖耀和好友(亦师亦友)张文奇、方正知等名师一同教授金属学课程。当时,全国大多院校采用的古里亚耶夫所著的教材较浅,唯有钢院采用深得多的舒丁伯格的金属学教材,徐祖耀和同事们为了备课经常讨论切磋,这进一步帮助他夯实了理论基础。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金相热处理系每周举行科学报告会和讨论会,全市的物理学者每两周都会聚集钢院。柯俊安排徐祖耀作了一次马氏体相变的报告,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后来,苏联专家来到教研组,徐祖耀一度代理教研室主任职务,每天忙于授课、行政和教学活动,经常及至夜半尚未成寐,虽身心劳累,但成长很快。凭借着刻苦的努力,徐祖耀很快就成为钢院学生们最喜爱的青年教师之一。许珞萍教授对徐先生的授课印象极深:“徐先生讲课完全脱稿,将艰涩的内容都讲活了,尤其讲到有色合金相图时,徐先生当场将极复杂的青铜相图全画在黑板上,可见备课时的认真和费力之巨,他所表现出的深厚功力,深受学生们景仰。”陈梦谪教授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出徐祖耀关于相变条件的讲述:“热力学条件是最基本的,强调它是必然性,而动力学讲的是整个过程,也就是可能性。只有热力学和动力学都具备的条件下相变才能进行。每一类相变都要经历孕育、成核、长大的全过程,一般来说新相的形成初期会有一个‘浓度起伏’和‘结构起伏’……”春风化雨润无声,徐祖耀当年精彩的授课影响了几批人,他们至今仍在应用先生教授的基本理论开展学术研究。
1961年,徐祖耀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冶金系。他认为“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只有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因此,教育是根本任务,“教师的天职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1962年,徐祖耀任金相教研室主任,把已在国际上兴起的热力学引入金属学课程,丰富了原教学内容。他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学心得和国际研究的进展和发展趋势于一体,于1964年出版了《金属学原理》教材,该教材被柯俊院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著作”,培养了一代人的成长。“文革”结束后,根据自己的前期研究和国际研究动向,他在国内积极提倡“材料热力学”,同时提倡大学生和研究生应接受包括金属、陶瓷和高分子在内的综合材料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不仅仅是单一体系的知识,并身体力行,亲自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材料热力学”和“材料科学导论”,开国内之先河。他撰写的《金属材料热力学》于1981年出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在此基础上合著的《材料热力学》于2000年出版。他主编的《材料科学导论》于1986年出版,这些教材在国内很有影响力。随后,徐祖耀又撰写《相变原理》研究生教材,于1988年出版,并于1991年第二次印刷和2000年第三次印刷,至今仍是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在短短的几年内,徐祖耀编写的教材连续出版,充分体现出他对教育的重视。为培养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按照徐祖耀的说法:“著书立说乃是教授之本分。”
徐祖耀培养研究生,可谓严格要求,尽心尽力。他改学生论文的认真程度令人惊叹,不仅修改内容,而且多次指出学生引用文献的页码错误。他要求课题组的教师,至少要阅读100篇以上国际文献,才能给研究生定方向。他极力提倡“学生阅读文献后不只是综述,而是要进行评述,这样才能有创新的思想”。他鼓励研究生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发挥特长、敢于创新。
徐祖耀除授课、著书和培养研究生外,还非常重视教学改革。1982年,徐祖耀首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时,积极推动教学改革。他提倡美国的“宽厚型”模式,不同于苏联的“单科型”模式,即加强理论基础和拓宽知识领域。徐祖耀要求本科生课程增加“量子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和相关数学课程,加强微观组织表征的实验课程,还有X射线衍射和电子显微学。这些教学改革对材料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徐祖耀力求把“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办成“大材料”,即包括金属、陶瓷和高分子三位一体的科系。至今他仍坚持提倡和宣传这一办学思想。20世纪末,北京科技大学邀请徐祖耀等院士作为专家对“大材料”的教育改革作了细致的评定。对专业教改,他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需要改进的方向,为我国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教育改革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一生“金相”情
大学授业期间,徐祖耀偏偏对金相学一门课程最感兴趣,不曾想这个感情一直延续逾60余年。
“文革”期间,徐祖耀和许多学者一样,受到审查等不公正的待遇。在被受审查期间,他仍然惦记着教学科研工作。在从事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和教材参编工作中,有机会接触专业期刊,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文献,了解材料科学近年的发展,不断地思索研究的切入点。他深知材料科学实验对材料研究的重要性,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既不能开展试验工作,也没有助手和其他必要的条件,唯有文献可查,有纸有笔,还有大脑可以思维。在这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选定不需要实验的“相变热力学”为研究对象,先从马氏体相变热力学着手,经过10年磨难,身心衰竭。1976年夏,他体检时被查出患肺结核,医生开出病假条,对这个诊断他安之坦然,还认为“因祸得福”,即“可以借此请长假,避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全部时间可以遨游于无限的思索和奋笔之中。可是,病痛的折磨一天天加剧,他仍然将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工作,在他的病床旁,堆满文献、笔记本和稿纸,不断地阅读、思索、计算,再阅读、再思索、再计算。手术前,他终于完成了“马氏体相变热学”的初稿。然而祸不单行,该年冬季,胃镜检查后医生怀疑他胃内长瘤,需要手术。他给领导的信中写道“此行生死未卜”,但其内心却未起波澜,看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他欣喜不已。研究中,他博采众家之长,对前人研究加以提炼,添加了母相协作应变能,进而使马氏体相变开始温度的计算得以成功。经胃切除3/4出院后,他稍作休息,又每天去上海图书馆,除完善“马氏体相变热力学”文稿外,还想在此基础上撰写一本完整的专著《马氏体相变与马氏体》。后来,他形容这段岁月是“不觉得度日如年,恰似如鱼得水”。由于当时不能向国外杂志投稿发表论文,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发表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随后在《金属学报》又发表4篇有关论文。后来,向国外杂志投稿发表论文的禁令开放后,他在国际主要期刊相继发表多篇论文。此外,《马氏体相变与马氏体》专著也由科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硕果,均来自于他在“文革”磨难期间的艰苦耕耘。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国家教育与科研逐步走向正轨的背景下,徐祖耀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组建了“相变理论及其应用”课题组,从此开创了他科学生涯最辉煌的时期。看书、阅读论文、与课题组成员讨论,做科研、学术报告、撰写著作和论文,他如饥似渴地工作。常人的娱乐休闲时间已被他不停的工作挤得无影无踪。1982年起,即便在任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系首任主任期间,公务繁忙的他也从不放松科研工作。他深知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科教兴国的责任不容松懈。徐祖耀似乎在寻找一种清苦中的甘甜。他常对组里的教师和研究生说:“做学问,一要有兴趣,二要耐得住清苦。”他几十年一贯清贫自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之中。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以及美国Emerson公司等十多个项目资助下,研究领域广泛,从马氏体相变扩展到贝氏体相变,从结构材料扩展到形状记忆功能材料,等等,取得了不少学术前沿的成果。因此,徐祖耀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如ICOMAT、国际贝氏体相变会议,国际形状记忆材料会议等)作主题报告、大会报告,小组主席乃至大会主席。2005年在上海成功举办的国际马氏体相变会议(ICOMAT),徐祖耀和柯俊、赵连城为大会联合主席,徐祖耀并作大会报告。他也应邀在西德、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大学及研究所作交流和学术报告数十次。
步入耄耋之年以来,作为资深院士,徐祖耀强国之愿不减。近十年来,他领导的课题组,一方面从事纳米材料相变方面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再次把研究中心转向钢铁材料。钢铁材料中不仅有丰富的相变理论有待研究,而且钢铁材料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他在撰写的综述性论文中指出:“我国钢铁年产量逾5亿吨,是钢铁大国。但高附加值的产品不多,能耗高,污染大,因此我国并不是钢铁强国。要使我国从钢铁大国变成钢铁强国,必须发展具有自主创新的工艺和新的钢种。例如,如果把钢材的强度提高一倍、两倍甚至更高,就可节约大量的原材料,显著地降低能耗和污染。”为此他更关注科研为社会服务以及产学研的结合。例如,基于节能的考虑,他提倡“钢的塑性成形与热处理一体化”,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多场(温度场、应力场和磁场)下的相变,并就此应邀在多种场合下作报告。他带领课题组积极开展具有自主创新的先进的高强度结构钢的研究,提出了具有足够塑性的超高强度钢的微观组织设计的原则。他在斯皮尔(J.G.Speer)等人提出的淬火和分配(Q&P)热处理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淬火—分配—回火(Q-P-T)热处理工艺”,从而克服了Q&P工艺的缺陷。通过和宝钢合作,课题组成员应用Q-P-T热处理工艺,首次研制出超高强度纳米马氏体钢,并被国际认可的新型先进高强度钢。随后课题组开展对不同中低碳含量钢的Q-P-T热处理的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Q-P-T钢不仅具有高强度,而且具有高塑性。相关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杂志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Q-P-T新工艺在工程上的应用也获得初步的成果。自徐祖耀提倡开展先进高强度钢研究以来,他不顾身体劳累,先后应邀在中国工程院学术会议、北科大名师讲坛等作学术报告。2008年,他带领课题小组成员,亲自赴山东莱钢牵头研究工作,使课题组和钢厂建立了合作项目,并和莱钢成立了高强度钢联合研发中心,他亲任联合研发中心理事会理事长。
徐祖耀始终有一个理念:科研理论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其应用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迄今,徐祖耀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他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600余篇,其中在国际杂志和会议上发表250多篇,在国内杂志上发表370多篇。科研成果“马氏体相变”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马氏体相变热力学”于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形状记忆合金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贝氏体相变热力学及机制”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专著《相变原理》一书先后于1988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著作类)一等奖和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著作类)三等奖,2000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科技进步奖,“铜基与铁基合金的马氏体相变及形状记忆合金效应”获2001年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fcc-hcp的半热弹性马氏体相变及其诱导的形状记忆效应”获2004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用徐祖耀的话来说,初学“金相学”,是从“冶金强国”愿望开始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它成为了自己的科学理想,愿意为之终身追求。“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干着这一行,要是在这行里有些成绩的话,应归功于开始有一种愿望,到后来一往情深……”他对“金相学”的研究从“一种愿望”发展到“一往情深”,不断在材料科学领域内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寂寞坚守”心
徐祖耀经常说:“世界上天才是少数,有成就者大多工作勤奋。做学问要甘于清贫,安于寂寞。”他自己治学几十年,常常以此自励。
认识徐祖耀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做研究以外,没有任何欲望。这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蜚声海外的学界泰斗,却一直到1995年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笑称他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有人称他是“抹上了灰尘的金子,既然是金子,总有一天要发光”。1995年之前,徐祖耀的名字从未列入上海交通大学申请院士的名单中,尽管此前他已获得各项国家级奖项,他却从不提起,而且他既无先进的光环,也无社会职务,甚至还不是博导。不愿做官,不谋发财,为人低调,以书呆子自称的他一直视责任重如山,视名利淡若水。在1995年申报中科院院士时,他已是一名退休教授,但他从未中断过他深爱的学术研究。“欲空未必空”,他对自己获得迟来的院士称谓如是评价。
徐祖耀奉行“活到老,学到老”的信条。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完整地听完苏联专家教授的“物理化学”课程。新中国成立前,因单位人事的变动,他失去了派往美国MIT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尽管如此,他毫不气馁,竟然自学完成了MIT研究生的主要课程。60年代,他已是国内著名学者,他仍去华东师大物理系甘当学生,进修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课程。80年代,他自学群论,并指导硕士研究生将群论运用到马氏体相变晶体教学中去,创造性地提出了由马氏体相变产生形状记忆效应的条件是获得单变体马氏体,并基于理论研发了新型的形状记忆材料。90年代,他向数学系教师学习,同时指导硕士研究生用孤立子理论演算和阐释了相变驱动力和马氏体长大速率之间的关系。他在国外经典著作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学习体会和评论,他说,“每读一遍就有新的体会”。至今,他仍保持勤奋工作的状态。在他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除了西面墙上挂着一幅斗大的“寿”字条幅外,俯仰四顾,都是书和资料。古有陆游著书巢,此时徐先生的办公室确实颇有几分相似。三分之一的沙发被成堆的书籍资料占据,茶几也俨然就成了这房间的第三个书桌。
徐祖耀生活非常简朴。20世纪80至90年代,徐祖耀住处的楼道里灯光暗淡,到处积满了灰尘,过道上还堆有户主的各种杂物。对于高度近视的徐祖耀来说,每天通过这段“荆棘密布”的路途非常困难,可是他从没有抱怨,悠然自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惬意。他的房子是一套南北向的三居室套间,由一条约五平方米的过道(所谓的厅)把三间卧室分隔成两南一北。“厅”内炊具占了一半,不能作为待客之地,因此只能把其中一间卧室改作客厅,剩下的两间作为卧室。房子谈不上装修,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老掉牙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大夏天为了防蚊,屋里门窗紧闭,只有吱吱呀呀的电扇送来一丝凉风。徐祖耀就是在这样简朴的环境下研习学问的。
徐祖耀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都有些“特别”。作为国内外知名教授,他经常受邀参加由政府机构或学术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出于对徐祖耀的尊敬,邀请的组织机构总是希望能尽到地主之谊,展现较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可是每到这个时候,徐祖耀总是表现得“不近人情”。学生谢春生就有过被拒绝的尴尬经历,但是他能理解先生的心思:搞学术、做学问不必迎合社会世俗,吃请花钱浪费太大,再则要作学术报告,提前还要做一些准备,吃一顿饭,估计至少耽搁两个小时,时间也赔不起。谢春生曾多次邀请徐祖耀到学校讲学,有一次,在出席国家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前几天,他应邀去作学术报告。期间,发生了一件小意外,徐祖耀的脚后跟被划了一寸长的口子,这一变故耽误了他去北京的行程。为此谢春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这次事故让徐祖耀错过了接受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不料徐祖耀却和声细语地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已通过学校请假了。我们做学术的不在乎领导的接见与不接见,主要是没有能参加国家技术发展计划的讨论,这点比较可惜。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还能补救得回来。”
徐祖耀曾经说过:“科学研究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推动国家和全人类的进步。”如今,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奋斗,实践了这个庄严的宣言。
六十余载,科学研究,成果惠四海;六十余载,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六十余载,著书立说,长卷育后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徐祖耀的一生正是阐释了“师”“范”的真正内涵,学界泰斗,耀人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