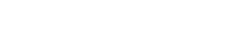柯俊,浙江黄岩人,生于1917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金属学、金属物理及科学技术史学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天津就读河北省立第一中学;1932年9月,入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预科;1934年,入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化工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至1938年毕业;1938—1944年曾在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负责民营工厂督迁工作,后至越南、缅甸、印度负责将用于工业发展的物资运往国内;194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1948年获自然哲学博士,从事合金中相变机理的研究,并担任理论金属学系讲师享有终身任命;1954年回国后,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教至今,先后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物理化学系主任、副院长。兼任:日本金属学会、印度金属学会荣誉会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教研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金属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原中国金属学会、有色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科技大学顾问,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

百川东渐入海,聚溪流不息;壁石屹立千仞,纳广博于有形。在满井村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位温和谦厚的老者,他大半生都致力于对钢铁科学领域的研究,默默耕耘,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他奉献智慧、挥洒汗水于三尺讲台,桃李天下,却孜孜不倦;年逾半百之时,开拓中国冶金与材料史研究,开启定量冶金考古研究的新篇章。他就是金属学、金属物理及科学技术史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柯俊。从青春年少到耄耋老人,强盛民族是其奋斗目标,三尺讲台是他献身的舞台。胸若空谷,性如幽兰,躬耕千顷,他的品性极像蓝色的海川,温和、睿智而渊博;他的作风又如淬炼的钢铁,严谨、热情而坚韧。
流亡颠沛求学路
柯俊出生于1917年6月23日,那日正值端午,石榴花开得灿若红霞,满树繁花绚烂至极。小时候的柯俊对新事物十分好奇,脑子里总有各样的奇思妙想,喜欢动手进行各式各样的小实验,在心中悄悄埋下了科研的种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14岁的柯俊正在位于沈阳郊区北岭的辽宁三中读高中一年级。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乱。伴随着接连不断的飞机轰鸣声和刺耳的警报声,白天柯俊和小伙伴们在教室里提心吊胆地上课,晚上大家藏到学校附近的高粱地里过夜。沈阳沦陷,学校被迫停课。北上已然不可能,柯俊无奈只能选择逃亡,投奔家住天津的小叔。逃难的路途充满艰辛,从沟帮子到锦州段的火车上,柯俊一直都站在踏板上,身体半悬在车外,仅靠双手紧抓着车门的扶手支撑身体,夜风嗖嗖地打在脸上,直到过了锦州他才终于挤进了车厢。一路颠簸,艰难跋涉到达天津时,柯俊早已蓬头垢面、饥寒交迫。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那时小叔已经回浙江老家养病,举目无亲的柯俊在陌生的城市里茫然失措。幸好正在寻找流亡学生的警察碰到了他,把他安排到了曹锟公馆里,与其他学生一起生活。不久,柯俊被分到河北省立第一中学(今天津三中),重新开始高中一年级的学习。1932年9月柯俊进入河北工业学院高中预科学习,1934年考入河北工业学院化工系,开始了大一到大三的大学学习。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响应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柯俊作为当时河北工业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与天津学联的学生干部们一起商讨响应北平地区的“一二·一六”运动,组织了天津地区的“一二·一八”大示威。“一二·一八”大示威游行中,柯俊高举“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与成千上万的学生一起,表达了汹涌的爱国热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华北告急。国民政府决定将大学生派往还没有被日军侵占的省市继续学业。满怀着对天津的恋恋不舍和对山河破碎的声声叹息,柯俊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四年级。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为保证学生安全,1938年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柯俊作为毕业班学生留在武汉。在经历了战乱和动荡之后,柯俊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为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兴盛而奋斗终生!
苦难不改报国情
1938年,在武汉城即将失守的焦灼时刻,柯俊从武汉大学正式毕业。正为生计一筹莫展之时,当时在经济部任职的恩师姚南枝把他推荐给了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柯俊由此来到国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负责民营工业工厂的迁转,主要工作任务是把长江中下游城市的重型机械、化学工业和纺织工程等设备迁到川陕滇贵等地,以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的柯俊充分意识到了这份工作的重大意义,他留在岌岌可危的武汉,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当中。在随后六年动荡的岁月里,柯俊辗转数地,先后在中国武汉、宜宾、昆明和越南、缅甸、印度等地开展工作。苦难的历程,记载着柯俊的勇敢、坚持和深切的爱国之情。
柯俊工作后,作为执行组组员,与组长李景潞及当地驻军一起督促厂矿拆迁。第一个任务是说服一个水泥厂厂主,将工厂拆迁到湖南常德。局势日益紧迫,长江下游吃紧,九江吃紧,武汉吃紧!日本人快打到武昌了,而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还有很多重要的设备没有完成搬迁。放心不下的柯俊特意又去了一趟汉冶萍煤铁厂矿下属大冶钢铁厂,他撬开了工程师屋子的大门,把地上剩下的东西仔细收集起来,把所有能拆的都拆掉带走。最让他心疼的是剩下两个100立方米的高炉无法运走,为了使高炉不被日本侵略军霸占,柯俊果断决定实施爆炸方案,并点燃了炸药,致使高炉彻底报废。很快,大冶便被封锁,柯俊等人立即撤退到武汉,开始搬迁武汉的纱厂、发电厂、纸厂。
1938年10月23日,武汉失守!22日晚,一无所有的柯俊在上级指示下离开武汉,怀着难以言说的沉痛心情,开始了他的再一次流亡。从武汉撤离到四川宜宾后至重庆,柯俊又接到新的任务:立刻赶赴越南负责民用工业物资的运输,保证正在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甘肃玉门油田的建设需要。于是,1938年底,他由昆明远赴越南。到达越南后,柯俊以其负责、干练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成立了运输队,并担任运输队队长,亲自将物资从越南运到昆明,使得民用工业物资在越南的转运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
1939年的春夏之交,柯俊再次奉命调回重庆,1940年又被紧急调往缅甸仰光。工作任务与在越南时相似,以缅甸为中转站将民营工业原料运往国内。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魔爪在1942年1月15日伸向了缅甸的土地,并迅速向仰光及缅甸北部推进。柯俊在安排好工作人员撤离后,只身一人留在仰光,全面接手缅甸的物资运输工作,一直坚守到仰光陷落前的最后一刻。
缅甸失守后,留给中国唯一能转运物资的途径只剩下了印度。1942年秋,柯俊又被调往印度,承担起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继续在美英等国的帮助下,将民营工业所需的原料经印度转运到国内;二是努力与印度的金融体系、工业体系建立联系,希望他们能在战后到我国投资建厂,帮助国内工业建设。困难从来都不是柯俊的对手,他立刻着手实施新的计划:每周一到周四在印度最大钢铁厂—塔塔钢铁厂参观学习,每周五到周日,则回到加尔各答市继续开展民营工业原料的运输工作。从英美等国运到印度的各种原料以及借款,都必须通过柯俊的验收后再从印度转运到昆明、贵州、重庆等新兴工业基地。先运什么,后运什么,也都由柯俊根据后方建设和国内发展的需要统筹安排。任务虽然繁重,但柯俊依然安排得井然有序,圆满完成了各种工作。
在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光里,柯俊亲历过国土的沦丧、同胞的牺牲、百姓的艰辛,心中不断涌动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和为国报效的勇气,从未停歇。
格致钢铁集大成
国民政府的困境,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的呻吟和挣扎……残酷的现实令柯俊深深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暗自下定决心: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自己的专长,用科技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当时有着雄厚的国力和科研实力。由于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有进口货物的业务往来,1944年该公司提供给经济部6个名额去英国学习。当年12月,柯俊被推荐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学习,师从当时著名的金属学家D.Hanson教授。柯俊在就读伯明翰大学研究生的第一年,就仔细研读了历届论文,了解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他先选择“铜再结晶”作为研究项目进行科研能力的训练,随后接受了金属学系工业实践性的课题,研究“低碳钢在焊接时的变化”项目。柯俊还接受了英国钢铁协会下达给D.Hanson的科研课题,阐明钢中过热和过烧机制。
为阐明“钢中过热和过烧机制”,柯俊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资料,寻找相近的理论方法;接着对这些刚刚理解的理论方法展开实验,但常常几个小时的观察记录后,却发现得到的数据不符合要求,实验宣告失败。多少个宁静的午后,柯俊与D.Hanson教授深入地分析讨论,再回到图书馆、实验室。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样不断失败总结再重来的过程中,柯俊创造性地通过金相方法,首次阐明了过热过烧的根本原因是硫化锰在高温加热时可以在钢中溶解,但在冷却时会在晶界或某个晶面上析出导致脆化。据此发表的论文《钢在过热过烧后的晶粒间界现象》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
1951年,柯俊首次发现并提出钢中贝茵体(或称贝氏体)切变位移运动,其转变受溶质控制的机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他运用此概念,利用我国富裕的钒硼资源,发展了高强度、高韧性贝茵体结构用钢。此外,他带领团队还首次观察到钢中马氏体形成时基体的形变和对马氏体长大的阻碍作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又系统研究铁镍合金中原子簇团导致蝶状马氏体的形成,发展了马氏体相变动力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柯俊阐述了钢中的无碳贝茵体形成的切变机制,《钢铁金相学》以他的姓氏将无碳贝茵体命名为“柯氏贝茵体”,而柯俊本人则被国外同行称为Mr.Bain(贝茵体先生)。
一直以来,无论海外留学还是归国执教,柯俊从未中断对合金中贝茵体相变机理的深入研究。1956年归国后,柯俊的《钢中奥氏体中温转变机理》获得当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成为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以来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奖。随后的研究中,他指导相1955级的赵家铮研究钢中魏氏组织提出和实验证明是由贝氏体切变机制相变的结果,共同写成《亚共析钢中α铁的魏氏组织》。20世纪60年代起,柯俊指导柳得橹、张学华等开展有色金属合金的贝茵体相变的研究。1970年起柯俊又指导贺信莱等紧密结合我国低碳高强贝茵体钢种的生产与发展进行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指导柳得橹、吴杏芳等人在不同的合金系中通过对不同方式形成的贝茵体形貌及特征的深入观察和细微分析。众多研究成果使柯俊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贝茵体相变的“切变学派”成为主流学派。
柯俊在到达英国的第二年便被校方聘请担任大二年级《冶金学与金属学的物理化学基础》课程的老师,并于195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终身讲师的任命。此时的柯俊早已展露了为人师者的风采,他思路缜密、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赢得了不同肤色学生的仰慕。
在英国进行了“铜的再结晶”、“低碳钢焊接时的变化”及“钢中的过热和过烧机制”三项研究之后,柯俊的博士论文内容也基本成熟,于1948年12月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学位。
繁重的课业之余,柯俊还积极参加了留英中国学生同学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他自告奋勇担任了留英中国学生同学会时事讨论会的联系人,在自己家中组织中国学生们聚会、畅谈。其中与柯俊来往密切的有就读于谢菲尔大学冶金系的李薰、张沛霖,剑桥大学的邹承鲁、李四光的女儿李林,还有在伯明翰大学的挚友王大珩、姚桐斌等。这些爱国学子身在彼岸却心系祖国,时刻以民族复兴为己任,鞭策自己不断进取,期待着回国报效的那一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海外的中华儿女欢欣鼓舞。1950年末,刘宁一、周培源、涂长望等到英国访问,希望柯俊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此前后,由于柯俊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等均先后向他提出邀请,都被他婉言谢绝。恩师姚南枝,时任台湾碱业公司总经理,也极力邀请柯俊去台湾任他副职,但面对恩师,柯俊唯有用“结草衔环,容图报于来世”的誓言谢绝。各种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都没有让柯俊有丝毫动摇。正如他对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史密斯教授说的:“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更不是最重要的。”
筹备回国期间,柯俊继续对合金钢、碳钢中奥氏体中温转变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考察了西欧的主要学校和工业研究所,为回国后开展全面研究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此外,柯俊还利用他在英国广泛的人脉,取得了德国马普研究协会的设计图纸,其中包括实验大楼和实验工厂的设计结构,并迅速寄回国,这为金属研究所短时间内顺利建成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临近回国之际,柯俊还订购了很多书籍和杂志,定期寄回国内。这些杂志记录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和论文,为我国金属科研和金属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借鉴和帮助。
师昌绪院士曾回忆说,1955年他看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图书馆有全套的JournalofIronandStell和PhilosophicalMagazine。而后连续几年,由国外寄到金属研究所的上述杂志都写着Prof.T.Ko(柯俊教授)的名字。“柯先生回国后虽然没来沈阳,因为教育界更需要他,但他对金属所的感情至深。在北京钢铁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中,在他的影响下,(向金属所)分派了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支撑着金属所的前进和良好学风的形成,也出了不少学科带头人,其中有三位院士和所长。”
金物桃李满天下
1953年10月,柯俊回国。高教部领导曾多次与他谈话,请柯俊认真考虑留在北京,可以选北京的科研院所或新组建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回国后搞科研就去研究所,办教育要到高等学校。前者轻车熟路,深入一点就容易出成果;后者辛勤耕耘,但是桃李满天下,影响更大。”导师D.Hanson教授的临别赠言音犹在耳。柯俊充分认识到钢铁工业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深知高等教育对培养钢铁材料人才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毅然来到了刚刚建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回国初期,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落后让柯俊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回想国外先进的科研理念和基础设备,柯俊脑海中的一个新想法出现了—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开设金属物理专业,这得到了当时的代理院长魏景昌的大力支持。1955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授权柯俊负责金属物理专业建立的相关事宜。
万事开头难。为了解和翻译莫斯科钢铁学院的相关学科知识,尽快制定出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情况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柯俊开始学习俄语,认真地查阅资料。与此同时,他先后成功说服了张兴钤和肖纪美两位同样留学归来的知名教授来到北京钢铁学院金属物理教研组任教,形成了柯俊、张兴钤、肖纪美、方正知四大教授为首的教学队伍。当时,教研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1961届学生开设专业课,但初创的金属物理专业既无教学大纲可循,也无教材可用。在这种情形下,柯俊、张兴钤、肖纪美、方正知四位教授迎难而上,参考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自编讲义开始授课。由于各位教授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并曾做出居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对知识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再加上他们授课内容丰富,声情并茂,学生们每次都意犹未尽,一再要求增加学时。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众多知名学府慕名派到钢院金属物理教研组进修的教师络绎不绝,四大教授声名远扬。同时,由于柯俊的努力,学校还安排了最好的基础课老师如著名的物理学家顾静徽教授、数学家刘景芳教授等给学生教基础课,可谓大师云集、名师荟萃。这使得金属物理专业在全国高校系统树立了极高的声誉,五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毕业生,为我国金属领域科学研究和金属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开启电镜教与研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子显微学一直在国际材料科学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电镜在金属研究方面的应用也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开展起来,到20世纪50年代电子显微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柯俊回国任教期间,大胆预测初露端倪的新型学科—电子显微学将会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于是,他在我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和发展的过程中高瞻远瞩,积极倡导并亲手组建电子显微学的师资队伍,专门开展X射线衍射晶体学和电子显微学的科研与教学。
1958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批透射电镜问世。柯俊立即与校领导谈话沟通,努力说服学校购置了第一批问世的四台国产电镜中的一台。虽然这台电镜分辨率只有10纳米,加速电压仅为50千伏,最高放大倍数为2万倍,但是在当时已经是学校最高端的仪器之一,与真空喷镀仪一起,开启了学校电镜科研、实践的新篇章。
“文革”期间,身处逆境的柯俊仍牵挂着我国电镜方面的发展,闻及国内相对落后的状况,他希望能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提升我国科研能力。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积极争取国家科委将新进口的JEM-7(后来改成日立H-11)拨给北京钢铁学院,后因“文革”干扰未果。1968年和1972年,柯俊又争取到当时冶金工业部科技司胡兆森司长的大力支持,购置了一台透射电镜(捷克产Tesla413型)与一台扫描电镜(英国剑桥产的S-250型)。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无疑是老一辈学者对学科建设的执著精神所创造的一个奇迹。后来,又有多台高级电镜落户北科大。在柯俊的悉心指导下,北京科技大学不仅成为我国材料科学最早开设电子显微学课程、最早出版电子显微学系统教材和最先拥有电子显微镜的大学之一,而且也是最早开展材料电子显微镜科研工作的高校之一,电镜的科研水平在国内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盛名远播。现在看来,正是柯俊当年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的举动,北京科技大学电镜研究才结出开创性的丰硕成果。
在做好电镜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同时,柯俊还一直致力于电镜人才的培养工作。为了缓解我国电镜领域人才奇缺的压力,促进中国电镜事业的长远发展,柯俊于1985年主持开办电子显微镜培训班,多年来共培训了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和各机构学院300余人。同时,柯俊还与钱临照、郭可信等31位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发起,向中国物理学会提出申请成立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并于1980年11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1999年电子显微镜学会登记在册的会员共有1537名,分布于不同学科领域,其中涌现出一批电子显微学专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8位。
柯俊就是这样一位站在科研前端的学者,回首当年,他的所识之广、所见之远,令人惊叹佩服。
冶史长河始泛舟
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辉煌而久远的历史,而在冶金技术发展的长河中却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文字记载和历史资料。1974年,北京钢铁学院受冶金工业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委托,编写《中国冶金简史》,柯俊作为“重要专家”参与编写工作。由于学校图书馆资料有限,资料搜集工作举步维艰。柯俊自觉地挑起了重担,带领大家放弃休息时间,组织小分队外出考察,坚守在空旷的学校里开展冶金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经历一年多的努力奋战,编写组最终在1976年底向科学出版社交了答卷,该书于1978年2月正式出版。
编写冶金简史的工作,让柯俊及其合作者在中国冶金简史的漫漫长河中畅游了一番,也开启了柯俊科研生活中崭新的一页。1975年,柯俊刚开始从事冶金史研究工作的时候,受到夏鼐先生的委托,鉴定一件足以轰动全球的文物—“商朝末年的铁刃铜钺”。柯俊用电子探针等先进技术对该文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件公元前14世纪的铁刃铜钺刃部是由陨铁制成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派人找到柯俊了解情况,希望诱导柯俊做出人工冶铁的结论。当时社会环境复杂,政治气候变化莫测。但柯俊始终坚持真理,巧妙地利用科学鉴定方法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最终说服工作组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并将鉴定结果公开发表,震惊了学界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后来柯俊先后进行了西晋朝周处出土的“铝片”和新石器时代的黄铜等的鉴定,这些鉴定都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柯俊以他独特的鉴定技术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博得了世界的认可。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柯俊的坚持努力下,冶金史编写组逐渐发展为学校的冶金史研究室、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建立了“科学技术史”专业,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科学技术史(工学)博士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一。多年来,研究所一直承担着国家科技部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以及国家文物局基础研究基金等多项重要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取得了许多科技成果,获得了国际国内社会的肯定和好评,和美、英、德、瑞、日、韩、澳等各国高校和博物馆建立了交流合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中,“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的历程”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荣获全球各冶金、金属学会联合举办的大学生研究生成果唯一的亚洲奖。面对如此卓越的成绩,柯俊却谦虚地说:“这都是全国各考古单位指导支持的成果。”
“请进来,走出去”
为了在国际学术前沿培养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柯俊凭借着自己在海外与国际上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建立的深厚友谊,秉承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为推动北京科技大学同国际著名院校的校际合作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倾注了巨大心血并做出了杰出贡献。
“请进来”,就是柯俊等学者利用自己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及个人感召力,把国内外材料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邀请到北京科技大学交流并讲学,并聘请一些科学家担任北科大名誉教授。如英国牛津大学Hirch教授和Christian教授、美国Cohen教授和Thomas教授、德国Hassen教授和Dahl教授,百炼成钢不惧难43柯俊瑞典Hiller教授,加拿大Purdy教授和Piercy教授,日本桥本初次郎教授等。柯俊还邀请了国内许多相关院所的著名学者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指导、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如郭可信院士、钱临照院士、李方华院士、彭练矛院士等。其中郭可信院士指导的物理化学系学生中,任罡、李慧林、邹晓东三位,成绩显著。他们在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人彼得·阿格雷和罗德里克·麦金农发现细胞膜水通道,对离子通道结构和机理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实验支持。
优良的师资队伍固然重要,而启迪学生智慧,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更是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柯俊为此积极地为学生拓展交流平台,在国内率先开设研究生学术讲座,邀请一大批国内外的专家为研究生介绍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动态,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科学家如黄昆院士、师昌绪院士、林兰英院士等。学术讲座已不单单是一种促进交流和获得最新知识的手段,它成为一种创新,一种传统,对提高学生素质起了巨大的作用。
“送出去”着眼于学科的长足发展,柯俊在学校的支持下,凭借个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先后推荐并派出周政谦、吴杏芳、柳得橹、王蓉、魏鎏英、陈清、孙永谦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到英国牛津大学、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瑞典查尔斯默斯工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日本冈山理科大学等著名学府,以访问学者或博士生联合培养的方式,进行电镜科研和材料学方面的科研协作学习,使得我国电子显微镜科研与教学水平迅速与世界接轨。
1979年柯俊访问德国亚琛大学时,在与达尔、勒克教授的共同努力下,首先促成北京钢铁学院与德国亚琛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并联合培养博士生。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学府与国外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合作关系,是中国高校开展国际交流的起点,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1年柯俊与学校其他领导赴加拿大访问,与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卢维高与珀迪教授共同努力,于1982年促成两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此后两校的协议又被纳入中加两国政府之间技术合作的协议中。自1982年起,北京科技大学每年派往麦克马斯特大学进修的访问学者、教师等多达数十人,这些老师回校后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84年经柯俊建议,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校长的大力支持下,北京科技大学每年都会派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教师到该校进修深造。
此后,在柯俊的努力下,北京科技大学先后与美国宾夕法尼亚、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法国图鲁滋大学等国际上23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加速了学校走向国际科技舞台的步伐。
教改探索“大材料”
20世纪80年代初,英、德、美等国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柯俊先后接待了这些代表团。代表团向柯俊传达:中国的工科大学培养出来的只是技师,不是工程师。目前高校培养的学生基础薄弱,只重视具体技艺,缺乏创新潜力。这一结论令柯俊深思。20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柯俊把目光集中到如何为21世纪的需要改革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上来。他积极奔走,潜心调研,多方呼吁开展教育改革,主动到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著名大学和许多用人单位调研,建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围绕高等工程教育开展研究,并和张光斗、师昌绪、路甬祥等院士一起承担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咨询课题》,并亲自将报告提炼成六个问题、六条建议,于1993年春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报告—《改革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增强我国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1996年柯俊在调研的基础上,在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共识和支持下,正式启动了旨在培养工科学生工程意识、创新意识、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大材料”专业试点班的教改课题。
为确保改革的成效,柯俊不但参与到每次课程设置的讨论会中,还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主持建立了“大材料”试点班的新型课程体系,体现“大工程”观念,并亲自参与制定了实验班教学计划的整体框架。柯俊亲自邀请国内外知名材料大师到“大材料”实验班讲课,以提高学生的学术视角;他还专程到宝钢协调、关注试点班在工厂的研究实践,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2000年,“大材料”实验班毕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实验班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96%,相当一部分学生后来都考上或被保送攻读研究生。对此柯俊说:“我们不打算把他们都放在学校里读,要把他们放在更为严格的环境中去造就。像现在左铁镛1、徐匡迪、郭可信、林兰英、严东生等一批院士都答应接手部分学生去培养,如果在这些著名的严师指导下能通过,那也可以说明我们本科教育的部分成功。”
1999年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的陪同下,专程看望柯俊教授。落座后,三句话不到,柯先生就将话题转到近几年一直挂在嘴边的北科大“大材料”专业实验班的教改问题。李岚清副总理风趣地说:“大材料主要应该是一个‘大’字,”并指出,“你们的教改实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新材料是我们下个世纪重点发展的领域。这是各种专业的结合,所以拓宽专业,加强基础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2001年,“大材料”教改成果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而今已过鲐背之年的柯俊仍然活跃在教育改革的第一线。先生曾题词:“在科学技术创新时代,创新者敢于创新、容许创新、有效创新是中华民族21世纪存亡、复兴的关键。创新者的素养、严谨的学风、创新思维、实践的能力、人文和科学的基础素质、有效的研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教育的核心。”
笑对人生显智慧
虽然柯俊在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保持着谦虚、朴素、和善、好学的作风,受到人们的深深爱戴。“未出土时先有节,已到凌云仍虚心”是柯俊面对学术勤奋精进、面对教育持之以恒、面对名誉淡薄悠远、面对生活豁达乐观的最好写照。他是真正的智者。
柯俊对待学术问题十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早在他在英国留学期间,面对学界对于“柯氏贝茵体”的高度评价,柯俊就表现得极为谦虚,他觉得贝茵体是30年代初美国人Bain等发现的,自己只是对它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并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进行命名。也正因这种谦虚的心态,才促成了他日后在该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并得到国际学者的广泛认可。
柯俊的生活像一湾清泉,简单而质朴。熟悉柯俊的人都知道,他曾有一辆28旧自行车陪伴他很长时间。虽身为院士,但他常常骑着这辆旧自行车,穿梭于校园中间。北科大毕业的潜伟教授曾说:“一次,我从清华打车回来,路过五道口时,天正下着小雨,远远望见一位老者推着28自行车在蹒跚行进中,走近一看,居然是柯先生,我请先生上车,他坚决不从,我只好下车陪他走回学校。他一直坚持骑他那辆我们看来都异常破旧的自行车。”如今,虽然柯俊因为年事已高无法再骑自行车了,但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里,人们常常仍然能看到一位略微驼着背、有些瘦弱但精神抖擞、气质非凡的老者,踱着步子在校园里走着,时常停下来跟师生们攀谈着什么,用手边比画着边讲述着,像是在指点迷津,眼神里透露着智慧的光芒。他就是和蔼可亲的柯俊先生。
柯俊对待身边的人都十分和善,以诚相待,平易近人。与柯俊接触过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他还常常告诉师生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一次,他从逸夫科技馆开会出来,见到当时看门的老王,就热情地上去打招呼,见到学生一脸诧异的表情,就说:“他很了不起,50年代在学校北门看门,见到当时苏联专家的车也敢拦下来,秉公办事,值得我们尊敬。”
柯俊对待生活中的挫折也表现得十分豁达坦然,很少有人知道看似精神矍铄、乐观健谈的他是一个曾几度闯过鬼门关的人。1998年11月81岁高龄的柯俊应印度金属学会的邀请,赴印度班加罗尔作“中国的金属文化传统”的特约报告,由于旅途劳顿休息不足,当他作完报告下台后就晕倒了,经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下壁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后经积极治疗,柯俊的心脏才奇迹般地建立了循环,病情逐渐稳定并得以康复。事后柯俊坦然地说,“自认为已经清除了自己身体内的两处隐患—胆囊结石和前列腺肥大,而忽视了心脏,这次是给自己敲了警钟。看来马克思还没有到收留我的时候。”2006年12月柯俊被诊断为直肠癌,在完成直肠开刀手术后,柯俊依然关心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主动请缨,要求听取研究生工作的进展汇报,最终征得他爱人和亲属的同意,规定每天与柯俊谈话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
谈到这样忘我的工作和学习状态,柯俊总说自己要小十岁,要用实际行动弥补“文革”十年的时光。一直以来,不论柯俊多忙、外出开会,总要挤时间去书店,看书、买书,在他家的书桌、书房、床上,堆满了书、百炼成钢不惧难47柯俊杂志、文件等厚厚的材料。他曾告诉家人,不要随便整理他的书房及书桌,他幽默地说:“我的书房、书桌摆放的书是长程无序、而短程有序。”为了赶上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柯俊在20世纪80年代就购置了一台计算机,坚持自学、使用,他是北京科技大学连通Internet网络的最早的用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柯俊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的誓言。
栉风沐雨,百炼成钢。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一息,但对于柯俊,对于中国的金属学界、冶金史学界,却是不平凡的百年。柯俊用他的勤勉、博大、坚韧和宽厚参与了我国钢铁事业由起步到腾飞的跨越,开拓了中国冶金史学从星火到燎原的成就,哺育了一代代学子从懵懂到功勋的成长,成为我国冶金教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